观点:强迫症不仅仅是洗手或整理作为一名患有这种疾病的历史学家,以下是我所了解到的
- 作者专栏
- 2025-02-02
- 141

(请读者注意,这篇文章包含对自杀、自杀和强迫性思想的明确讨论。如果您需要支持,请在文章末尾提供联系方式。)
马特说,12岁时,“不知怎么地”,他开始反复思考是否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每次看到刀,他都会问自己:“我会刺伤自己吗?”或者,当他走到一个岩架附近时:“我要跳下去吗?”
马特听说过很多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事情,他认为这一定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让人困惑,他说,“我没有自杀的感觉,我真的很享受我的生活。我只是非常害怕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不久之后,马特听说了一部臭名昭著的禁片,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像主人公一样,可能是一个连环杀手。这些想法“不断出现”,他会躺在床上想象各种场景,试图弄清楚自己是否“疯了”:“我真的需要帮助。我不知道该跟谁说。但我没有想到这是强迫症。”
强迫症(OCD)是21世纪重要的心理健康诊断。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列为十大致残疾病之一,导致收入损失和生活质量下降,强迫症经常被列为全球第四大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仅次于抑郁症、药物滥用和社交恐惧症(对社交互动感到焦虑)。
然而马特告诉我,他对强迫症的了解都来自于日间脱口秀节目,“人们每天洗手1000次——都是些外在的极端行为。”那感觉不像是他所经历的。
约翰(化名)在2011年出版的《控制强迫症》(Taking Control of OCD)一书中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在一位同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他“满脑子都是”自己可能会对自己做些什么。每次过马路时,约翰都在想:“如果我停下来被公共汽车碾了怎么办?”他还想谋杀他所爱的人。约翰回忆说:
“尽管我尽力了,但我就是无法将这些想法赶出我的脑海……当我试图向我的女朋友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找不到一种方式来表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时,我认为强迫症就是反复检查你是否锁上了前门,抽屉是否整洁。”
尽管强迫症在当代社会很流行,但马特和约翰的经历反映了这种疾病的两个重要特征。首先,强迫症的刻板印象是一种清洗和检查行为——强迫方面,临床上定义为“一个人感觉被驱使去做的重复行为”。而这种痴迷——通常被定义为有害的、性的或亵渎性的“不想要的、不愉快的想法”——被认为是模糊的、令人困惑的、无法识别的强迫症。
因此,经历强迫性思想的人常常无法识别自己的症状是强迫症——他们在临床环境中看到的专家也常常无法识别。由于对这种疾病的错误描述,具有非典型、不太明显症状的强迫症患者通常会在10年或更长时间内未被诊断出来。
约翰去看全科医生时,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他回忆说,全科医生更关注的是他的痛苦带来的看得见的影响——食欲不振和睡眠模式紊乱。那些思想仍然是看不见的。正如他所说: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告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想杀死你爱的人。”
即使是像我的朋友艾比这样的“教科书式”强迫症患者,“强迫症也只是冰山一角。”艾比在12岁时就有了自我诊断的能力,当时她经历了洗手和锁门的强迫症。她说,人们仍然认为她是“爱洗手的艾比”。
现在,她告诉我,“我意识到我对洗手没有兴趣——我是一个很邋遢的人,我不介意别人邋遢。”她的行为并非出于对清洁的热爱,而是与一种更可怕的强迫性想法有关:“如果我要伤害别人怎么办?”
临床指南,如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提供的指南,将强迫症定义为兼具强迫和强迫的特征。那么,为什么马特、约翰和艾比遇到的困难——认识支配他们生活的内在思想——似乎如此普遍呢?
从16岁开始,我也被后来与强迫症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所折磨,但这些想法一开始是看不见的、折磨人的。201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看不见的痴迷》(The invisible Obsession)的文章,描述了我在学习中途离开大学的经历,原因是一个念头积聚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我最终攻击自己的身体,试图消除它的力量”。我写: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一直受到强迫性思想的折磨,可以肯定地说,(强迫症)远非干净的手。”
从我十几岁开始,我的执念就有很多形式。一开始,我开始怀疑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存在,我的父母是否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我是否想伤害——而且是对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我的狗构成威胁。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反复思考一个人、一场冲突或其他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情是什么感觉。但对于那些有强迫性想法的人(确诊或其他),这与简单的“过度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我在文章中试图解释的那样:
当这个想法跃过你的脑海时,谈话就会中断。其他话题似乎不那么重要了,给自己的时间提供了评估、分析和寻找想法“真实”的证据的空间……[困扰]就像战斗:你把你的想法推开,它们会以两倍的力量回来。你花时间试图避开它们,它们却到处冒出来,嘲笑你逃跑失败的尝试。”
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进行每周的治疗,直到我觉得能够向我的治疗师——一个我认识多年的人——说出我的强迫症想法。我不愿意敞开心扉,这不仅与我对禁忌内容的羞耻感有关,也与我无法将这种想法视为一种公认的疾病的一部分有关。
强迫症是由什么构成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理解和误解它,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些问题引导我研究强迫症是如何被认可并归类为一种精神健康障碍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从伦敦南部一群有影响力的临床心理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做出的研究决定中获得重要的见解——这揭示了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这么多人仍在努力认识和理解我们的强迫性思想。
精神疾病的种类在时间上并不稳定。随着医学、科学和公众对疾病的认识发生变化,人们对疾病的体验和诊断方式也在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强迫”和“强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相反,它们出现在一系列精神病学分类中。例如,在20世纪初,英国医生詹姆斯·肖(James Shaw)将语言强迫症定义为“一种大脑活动模式,其中一种思想——主要是淫秽或亵渎——强迫自己进入意识。”
根据肖的说法,这种大脑活动可能出现在歇斯底里、神经衰弱或妄想的前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经历了“无法抗拒的、淫秽的、亵渎的、难以言说的想法”的女人——被诊断为强迫性忧郁症,一种“精神错乱的形式”。
这种症状源于肖所定义的“神经衰弱”,这种解释反映了19世纪更广泛的观点,即强迫性思维表明神经系统脆弱——要么是遗传的,要么是由于过度工作、酗酒或滥交行为而削弱的(被称为“退化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肖没有提到任何形式的重复行为与这些言语强迫症有关。
在肖伯纳写作的同一时期,精神分析学的奥地利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发展了他的精神分析分类“zwangsneurosis”——在英国被翻译为“强迫性神经症”,在美国被翻译为“强迫性神经症”。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嗔”指的是在未解决的童年冲动(爱与恨)和批判自我(自我)之间的压抑冲突中出现的持续的想法。
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案例研究发表于1909年,以“鼠人”为主题,他是一名前奥地利军官,拥有各种复杂的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他一直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老鼠惩罚的受害者,这是一位同事向他讲述的。病人还表示,如果他有某些愿望,比如希望看到一个女人裸体,他已经去世的父亲“一定会死”。
弗洛伊德将鼠人描述为参与“仪式防御系统”和“充满矛盾的精心操作”,这被一些人解读为会成为强迫症的行为方面。然而,弗洛伊德的客户的“防御”和强迫症的强迫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包括前者主要涉及思考而不是行动,并且绝不是一致的或刻板的。
“强迫性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范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被采纳和修改,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精神病学教科书中一个主要的诊断——但定义不一致。直到20世纪50年代,“痴迷”和“强迫”这两个词在精神病学著作中被交替使用。奥布里·刘易斯(Aubrey Lewis)是战后英国精神病学的领军人物,他将“强迫症”描述为由“强迫性思想”和“强迫性内心言语”组成的。
和弗洛伊德一样,刘易斯也提到了强迫症患者的“复杂仪式”——比如病人“总是把自己置于最大的麻烦中,以确保自己永远不会无意中踩到虫子”。但他警告说,“把任何形式的重复活动与强迫症联系在一起是危险的”,他写道,“这当然不能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判断。”
强迫症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以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形式出现,并在1980年和1994年被列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诊断和统计手册(通常称为DSM-III和DSM-IV)的第三和第四版,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精神障碍。
可见的和可测量的行为在强迫症分类中的中心地位——尤其是洗衣服和检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临床心理学家在伦敦南部的精神病学研究所和莫兹利医院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在南非心理学家斯坦利·拉赫曼(Stanley Rachman)的指导下,强迫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类别中包含的一系列复杂症状被分为两类:“可见的”强迫性仪式和“不可见的”强迫性沉思。虽然拉赫曼和他的同事们对强迫行为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但强迫行为却被置于次要地位。
例如,在他们对10名被诊断为强迫性神经症的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强迫症状必须出现才能进入试验,抱怨沉思的患者被排除在外”——这一说法在随后的实验中不断得到重申。
事实上,这项研究并不仅仅要求患者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可见强迫。这10名患者都有“明显的洗手行为”,这被认为是“最容易”进行实验的症状。同样,第二轮研究只包括那些有明显“检查”行为的病人,比如门是否打开了。
在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拉赫曼提出了他采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解释了“强迫性沉思者由于其主观、私密的本质,给临床心理学家带来了特殊的问题。”他认为,这与“强迫性神经症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强迫行为——形成了对比,后者可以更容易地处理。”它是可见的,具有可预测的质量,并且在动物研究中有许多可重复的类比。”
拉赫曼认为强迫症是“可见的”和“可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临床心理学在英国,特别是在莫兹利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为了将他们的实践与现有的精神病学(受过医学训练的专门从事精神健康的医生)和精神分析(源自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的精神健康专业区分开来,这些早期的临床心理学家将自己描述为“应用科学家”,他们将科学方法从实验室带到临床环境中。他们的科学观念植根于经验主义,强调可见性、可测量性和实验性。
作为对实证科学的承诺的一部分,这些临床心理学家采用了一种源自20世纪行为主义的焦虑模型。这种对可观察行为的关注被认为比精神分析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精神分析处理的是“不可验证的”和“不科学的”思想和思维领域。
因此,当强迫性沉思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重新获得关注时,它是通过可见的强迫行为的镜头。拉赫曼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把“精神冲动”(比如在一个坏想法之后说出一个好的想法)称为“等同于洗手”,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这些想法本身的重要性和内容上。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临床心理学受到认知心理学家(那些关注思维和语言的心理学家)的压力,因为它对行为的简化关注。但是,尽管这一举措包括认知方法,可见行为强迫的中心地位仍然是强迫症在文化和临床领域的特征。
这一点在媒体对强迫症的描述中最为明显——Dana Fennell等文化学者接受了这一批评,她研究了强迫症在电视和电影中的表现。
最近对大卫·贝克汉姆和他的大量整理工作的宣传,对强迫症的典型描述并没有帮助。当我问艾比如何看待媒体对贝克汉姆强迫症的关注时,她回答说:“这太无聊了。这种表现总是被认为是强迫症。”
这种强迫症的典型写照也与它的治疗方式有关。如今,英国的“黄金标准”治疗是暴露和仪式预防(ERP)的行为技术,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认知疗法相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拉赫曼和他的同事们专门研究具有可观察行为的患者,ERP从他们的实验中获得了认可。
他们的一项重要研究涉及莫兹利医院(Maudsley Hospital)反复洗手的病人。他们被要求触摸狗屎的污渍,把仓鼠放在他们的袋子里和头发里,同时被禁止洗澡的时间更长。
这样的实验再次受到可观察性和可测量性的支配。ERP治疗的“成功”——以及它被认为比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方法优越——通过减少患者明显的洗手行为得到了证明。
今天,如果你被精神病医生诊断为强迫症,并通过NHS接受强迫症专家治疗,你很可能会被告知要接受与20世纪70年代住院病人实验相同的ERP程序:触摸一组你害怕的东西(暴露),同时阻止你从事通常的强迫行为。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强迫性思维。病人被要求识别出他们的困扰,然后要么让自己暴露在令人烦恼的情境中,要么在不参与“精神强迫”的情况下在脑海中重复这个想法——比如数数,用好的想法代替坏的想法,或者试图“解决”困扰的想法的内容。
当然,这种形式的行为疗法对治疗强迫症症状非常有帮助。在经历了14年的ERP之后,艾比说她已经“养成了很多不屈服于自己(清洗和检查)冲动的做法。”
我还发现这种方法有助于减少我的强迫性想法的威胁性。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我想伤害我的家人”或“我真的不存在”,而不是真正去解决这些问题,减少了我花在沉思上的时间。
然而,作为ERP的大力倡导者,Abby也观察到“有时当我摆脱了强迫,并不意味着我只是摆脱了痴迷。”虽然“外在的强迫”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思维停止了循环和精神追问。”
一些当代临床医生将ERP称为一种“打地鼠技术”——你摆脱了一种症状(痴迷或强迫),另一种症状又冒了出来。ERP是围绕减轻可见症状而设计的。
ERP经常伴随着认知治疗技术,比如认知重组(识别信念并提供支持和反对它们的证据),或者被告知强迫是“只是想法”,它们是没有意义的,你不想实施它们。
尽管认知行为疗法(CBT)和ERP在科学试验中取得了成功,但2021年的一项主要证据综述质疑,这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的效果是否被夸大了——这反映了被指定为“治疗抵抗”的强迫症病例的高比例。
我也相信强迫症的当代治疗有一些关键的局限性。暴露(ERP)技术起源于临床心理学家根本不考虑思想的时期,而CBT则认为强迫性思想的内容不重要。和我一样,马特也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只能帮到你这么多”,他解释道:
“部分原因是(CBT治疗师)过于相信思想没有意义……(他们)治疗你的症状,一旦这些症状消失,你就应该继续你的生活。”我没有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我整个人生的背景下思考(我的)沉思。”
自从十年前我第一次为《重新思考精神疾病》写关于强迫症的文章以来,我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实证明,思考强迫症的历史发展和分类,让我对这种被广泛误解的疾病有了更大的释然感。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受当前概念框架的束缚,更能思考我认为对如何成功管理我的强迫性想法有帮助的东西。
例如,尽管从小就被警告远离精神分析(我妈妈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而心理学家通常是强烈反对精神分析的!),但我发现精神分析对我的想法非常有帮助。
这是因为CBT通常只关注当前的症状,而不去研究它们的含义,也不去研究它们与你个人历史的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这与我想要思考过去的愿望产生了冲突。相比之下,精神分析将强迫性思想置于历史中——指出童年是心理发展的关键点。我已经能够理解,我的强迫症是童年时对亲人死亡的深切恐惧的结果,由此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控制欲。
十几岁的马特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去了公共图书馆,拿出一本弗洛伊德的读本。他形容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可能读到的最糟糕的东西”,因为这让他相信“我真的有所有这些(杀人自杀)冲动,我所有的恐惧都是真的。”
尽管有这样的经历,但在接受社会工作者培训期间,他“进入精神分析领域,作为思考治疗和思考自己经历的另一种方式”。对他来说,精神分析揭示了“强迫症如洗手”形象的对立面。
相反,他说,它集中在“内在的痴迷”方面,向他展示了“思想是如此强大,它可以产生很多想象的恐惧”。这也让他看到了“强迫症症状与我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
精神分析思想中特别深刻的是对人类经验核心的复杂性和不可知性的接受。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人文学科教授杰奎琳·罗斯写道:
“精神分析开始于一个逃跑的心灵,一个无法衡量自己痛苦的心灵。也就是说,它始于认识到这个世界——或者弗洛伊德有时所说的‘文明’——对人类主体提出了难以承受的要求。”
这种“心灵在飞翔”的想法帮助我思考了我的困扰——我的父母是否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会伤害我爱的人吗?——考虑到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是一场既无法实现又可以理解的确定性和控制权之战的一部分。
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不是根除症状,而是揭示人类必须处理的难题。马特把精神分析称为承认“一种思想的混乱……我发现精神分析的观点是接受自己的混乱非常有帮助。”罗斯同样将精神分析描述为“在处理我们制造的混乱方面与家务相反”。
在英国,精神分析在NHS服务中被拒绝。我相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临床心理学家在20世纪后期开发出治疗强迫症的行为疗法时对其进行历史批判的结果。
虽然洗手和检查等强迫行为被广泛认为是强迫症的“代表”,但拥有强迫思想的痛苦经历仍然很少得到承认和讨论。这种想法带来的羞耻和困惑,再加上被误解的感觉,使这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强迫症的误诊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
我的强迫症历史博士学位也向我展示了心理学研究如何塑造我们对诊断类别的看法,从而塑造我们自己。虽然心理学对客观性、经验主义和可见性的承诺为临床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我的研究揭示了对可见症状的经常独家关注有时如何胜过对具有强迫性思想的复杂体验的欣赏。
我第一次见到马特是在2019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强迫症社会会议上,他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强迫症的多重含义”的演讲。我们讨论了自己对这种疾病的经历,以及我们认为历史、精神分析和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强迫症。
马特当时34岁,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大声说出内心的东西,并听到别人谈论它”。回忆起他当时的感受,他继续说道:
“我感到非常激动和悲伤。这种孤独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以至于我已经不再注意它了。然后摆脱孤立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让我意识到这有多糟糕。”
公司提供
nversation
本文转载自The Co在知识共享许可下的对话。阅读原文。
引用观点:强迫症远不止是洗手或整理。作为一名患有这种疾病的历史学家,以下是我所学到的(2023年12月8日)从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3-12-viewpoint-ocd-handwashing-tidying-historian.html检索到的2023年12月8日
作品受版权保护。除为私人学习或研究目的而进行的任何公平交易外,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任何部分。的有限公司
内容仅供参考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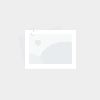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