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人一直投票给工党,但我的孩子们计划这样投票
- 经验分享
- 2025-01-24
- 145
我曾经被称为“忠诚的”工党支持者。1949年,我的父亲艾伦·曼宁(Alan Manning)在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现在的帕克斯)争取劳森(Lawson)的新席位,但后来失败了,于是我就怀上了我。我出生时,他正准备在1951年那场被匆忙称为“反共”的选举中再次倾斜,尽管他的选票份额有所增加,但他也输了。工党几乎是我DNA的一部分。

1972年,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以“是时候了”(It’s Time)赢得了令人难忘的选举胜利,当时21岁是投票年龄。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为工党分发投票指南卡片,并主持唐的派对(结果各不相同)。
众所周知,我父亲对亚瑟·考威尔(Arthur Calwell)领导的工党(Labor Party)非常失望,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他宣布将投票给自由党。当他投完票走出投票站时,他耸了耸肩。
“我做不到,”他说。“我想在Lib旁边画个‘x’,但我的手开始颤抖,我无法保持铅笔的静止。”
“你做了什么?”
“我当然投了工党的票。”
甚至有人认为,在过去,我是根据未来伴侣可能会投票给哪个政党来决定我的恋爱关系的。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如果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工党家庭,那就很接近事实了。直到现在。我的孩子们都不支持工党。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曾与工党调情,但求爱已经结束。

他们的年龄从40岁到21岁不等。他们代表了年轻选民的一个公平的横截面。不仅他们对现代工党感到失望,他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工党的议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们兴奋,更不用说如何起诉了。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具有社会良知的进步思想家。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政治上很活跃。他们关心这个国家和它的未来。他们担心气候变化。他们认为工党做得还不够。他们担心加沙,认为工党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试图迫使该地区结束正在发生的野蛮行径。他们担心公共教育的未来,无法理解工党政府如何让公共教育半途而废。他们问我,在公共教育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工党怎么会签署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潜艇协议,把国防决策从我们手中夺走。
“对不起,爸爸,但我支持绿色”,这是他们经常重复的一句话。
我可能出生在工党,但我也受到工党的启发。惠特拉姆,霍克,基廷。他们似乎都对这个国家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愿景,让我们想和他们一起冲破障碍。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带着向议会发声的愿景走出了街区。他表现出了绝对的承诺,直到投票日。但他没有攻击反对党出于政治动机而决定取缔《声音》,而是躲进了自己的壳里。
我的孩子们都评论工党的胆怯,并问:“他们代表什么?”我努力想要给出一个答案。
工党已经脱离了年轻人。各派系的阴谋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谨慎行事似乎是幕后的一个好选择,但这不会鼓励年轻人参加竞选,更不用说投票给他们了。
正如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所表明的那样,年轻人、女性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已经准备好为一个愿意为他们所信仰的东西而献身的政党而战。气候控制、土著权利、支持公共教育、负担得起的住房、一个既支持以色列生存权又承认巴勒斯坦生存权的加沙解决方案、一个明智的药物改革方案。
除非发生这种情况,否则我家支持工党的悠久传统可能会被打破。
内德·曼宁是一名作家、演员、教师。他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他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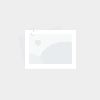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