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口普查的粉丝,但作为一名酷儿家长,我的家庭仍然不算数
- 生活常识
- 2025-02-06
- 130
这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但人口普查之夜让我兴奋不已。拍摄澳大利亚每个人的生活和家园的大胆想法深深吸引着我,我一直喜欢在这个充满希望的项目中扮演一个小角色的感觉。
人口普查数据帮助我们了解和预测在我们如何建立家庭、确保工作、维持家庭、接受教育、实践信仰等方面的变化,包括在弱势群体中。但为了保持这些数据的相关性,我们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

做出改变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为什么多年的咨询投入到一套简单的问题的发展中,这些问题涉及性、性别、性特征的先天变异和性取向。他们的加入将确保澳大利亚的每个人都能准确地完成人口普查,包括我的家庭。
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人口普查之夜的感觉。我可以看到自己融入了那个时候我最熟悉的地方:作为一个双亲家庭的老大,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的世界在一起。
当我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时,这种兴奋并没有减少,即使我的家庭生活模式看起来有所不同。在新千年之初,我们当时所说的“同性关系”很少在参与教育、就业、医疗或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所需的任何文书中得到承认。就连Centrelink也不认为同性伴侣同居是事实。人口普查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不完整、不充分,但又似曾相识。
我的孩子出生后,人口普查开始变得严峻起来。我知道,对于两个幸运的澳大利亚小孩来说,我们的家庭是安全而充满爱的(尽管非常吵闹)。但在人口普查之夜,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可能被编码到可用的选项中。从那以后,我也有过一段不舒服的经历:作为一个非二元性别的人和父母,我填写了一份人口普查表格,感觉夹在我的公民身份和我个人的自我意识之间。
因此,得知政府决定不继续在2026年人口普查中纳入新问题,感觉像是一种背叛。充满愤怒的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个在我们社区的大力支持下投票的政党会选择故意继续从我们最重要的国家数据集中删除历史上有害的内容。
上周五,当首相同意测试一个性取向问题时,他的“后空翻”受到了欢迎,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沉痛。自从婚姻平等以来,我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即使性取向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多样性形式,与性别认同有关的差异,以及与先天性特征(与性别和性取向完全不同)的差异,仍在继续积极减少。
更让我沮丧的是,如果把这些问题包括进来,我的知识就会受益。如果没有他们,至少到2032年,每一项由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带有性别成分的决定(仅举一例),从大规模的项目设计到本地化的服务提供,都将仍然是基于猜测。
上世纪70年代,当我的父母开始代我完成人口普查时,他们对一个全新的澳大利亚充满了希望。他们是坚定的工党选民,他们毕生致力于保护我们的环境,治愈殖民、强迫移民和贫困造成的社会危害。我们现在知道,要有效应对这些和许多其他政策挑战,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数据。这些见解帮助我们了解澳大利亚人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定位他们的生活和家庭,这对于实现社会凝聚力,社区福祉和适应变化至关重要。
我的孩子们都快长大了,所以如果不按计划在2026年把这些问题加进去,我就错过了在他们还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完成一次真实描绘我们家庭的人口普查的机会。但是,在一项声称代表我们所有人的调查中,将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排除在外,除了会造成个人伤害之外,这种选择还意味着将政治上的适口性置于履行法定义务的责任之上。
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酷儿、变性人或天生有性别特征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充分参与我们下一个大胆而充满希望的人口普查之夜。
克里斯蒂·纽曼教授是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的副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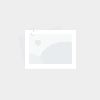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