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扩音的不可阻挡的崛起
- 生活常识
- 2025-04-10
- 137

最近我买了一些贵得离谱的助听器,目的是在嘈杂的餐馆里帮我解决问题。这让我开始思考,现代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过滤摄入的噪音。这是一笔大生意。随着警笛的呼啸、漫威大片和摇滚音乐会的轰鸣超过法定分贝水平,控制音量已经成为一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从硅胶微粒、音量控制旋钮到无线耳塞,一切都在辅助着这一过程。
音乐厅和歌剧院仍然是人们所谓的“自然”声学的避风港,在这些地方,用反射和吸收材料平衡凹凸表面的炼金术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回响的温暖可以与清晰共存,耳语可以传播到呐喊。在这方面,伦敦有幸拥有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和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和巴比肯音乐厅(Barbican halls),如果不是观众,通常被认为对表演者没有帮助)。尽管在这样的场地里,古典音乐家没有电子扩音,这仍然是一种尊严——他们拒绝,就像它一样,用仿生学的助音作弊——但这是一个乔公众永远不会给予他们信任的原则。但是,如果把像莉莎·戴维森这样的瓦格纳式女高音,在未经修饰的情况下,与阿黛尔这样的歌手一起演唱,乔就会被后者相对微弱的声音所震惊。
在影院里,这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唐纳德·沃尔夫特(Donald Wolfit)或艾伦·霍华德(Alan Howard)的宏伟咆哮,有机地产生和投影,是过去的事情。寻找片名中间的“音效设计师”:这可以证明演员们将通过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纸进行交流,这层玻璃纸给他们所说的话赋予了完全人造的光泽,使他们能够低声说话,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喃喃自语冒充情感真实性。坦率地说,在很多情况下,这有点欺骗,这对观众也不好,让他们更依赖于听觉上的无皱纹ps假。
对于音乐剧来说,这种做法当然是合理的,因为即使是最努力的演出歌手也需要在每周8场以上的演出中谨慎地使用声带(歌剧歌手最多只做3场)。1951年,玛丽·马丁(Mary Martin)在德鲁里巷(Drury Lane)出演了一部未经改编的《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一年内没有停过一场戏,但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较小的坑乐队、更严格的声乐训练以及期望值较低的观众是这种韧性的部分原因。)
放大的声音是如何或何时传播的,这是一个谜。然而,我们确实知道,1958年在德鲁里巷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使用了一排地板(或“浮动”)麦克风:根据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的回忆录,这些麦克风产生了一种放大的声音池,不幸的是,这些声音往往会捕捉到各种各样的杂音,尤其是雷克斯·哈里森(Rex Harrison)持续的肠胃胀气。1961年,在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芭蕾舞演员斯维特拉娜·别里奥索娃(Svetlana Beriosova)在跳弗雷德里克·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的《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时被要求背诵一些诗歌,一个原始的人体麦克风爆炸了,烧毁了她的服装。五年后,芭芭拉·史翠珊凭借《妙女郎》风靡伦敦。由于担心自己小得惊人的声音传不出去,她在乳沟里戴了一个麦克风——剧组里的其他人都不允许扩音。到了20世纪70年代,诸如《Hair》和《Evita》之类的摇滚音乐剧更加自由地使用了手持麦克风,重现立体声系统的高保真音质成为了目标。
今天,完全挤奶是音乐剧的标准。每个表演者将被单独连接到一个巧妙地隐藏在发际线上的微型耳机上,通过电缆连接到绑在背部或大腿上的发射器上,并通过礼堂后方的控制台与精心放置的扬声器进行混合。这是一件微妙的事情。你不能选择性地麦克风:麦克风一个,你必须麦克风所有,以避免双层效应。行业领导者Autograph Sound的主席特里·贾丁说,让耳机远离汗水是“最大的敌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汗水会掩盖高频的声音。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反馈着色”——麦克风实际上是在自我呼应。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会改变声音的方向,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
贾丁坚持认为,为观众提供一个巨大的助听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说,我们与其说是在提高音量,不如说是在营造一种氛围。他指的是《深夜小狗奇事》(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和《小巷尽头的海洋》(the Ocean at the End of the Lane)等奇幻剧的成功所带来的恐怖音效。杰米·劳埃德、卡蒂·米切尔、罗伯特·艾克和西蒙·麦克伯尼等导演都全心全意地拥抱了这项技术的潜力,尽管没有人能像马克斯·韦伯斯特那样走得那么远,他在唐马仓库制作的《麦克白》要求观众戴上双耳耳机,每一个幽灵般的吱吱声都通过无线电以超真实的三维强度传播。即使是契诃夫的单人版戏剧也可以被电力装置覆盖:在安德鲁·斯科特的《万尼亚》中,声音设计师丹·巴尔弗在斯科特的衬衫领子上缝制了两个麦克风,并在整个场景中植入了像苏联窃听器一样的隐形麦克风。“一个是水壶,一个是水槽,一个是枪,一个是门,一个是节拍器,两个是钢琴,三个是窗帘栏杆”,等等,使斯科特与之互动的一切都“砰”地一声,与他放大的说话声音齐平。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家剧院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然”的声音。它的奥利维尔礼堂(Olivier auditorium)一直存在声学问题,那里的混凝土墙使上层的可听性降低。人们尝试过各种结构上的改变和干预,但都没有成功。大约20年前,管理层屈服于头戴式麦克风——或者用他们委婉的说法是“扩声”。现在在利特尔顿和多尔夫曼礼堂的制作中也无处不在。反对电子语音魔法的最后堡垒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极少数情况除外”)和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容量为300人的阿尔梅达将在《岁月》中使用它,演员阵容为5人。这有多重要?在过去,把自己的声音传到观众席后面是一种职业荣誉。当被问及成功表演的建议时,号手罗伯特·斯蒂芬斯(Robert Stephens)轻快地回答:“大声说出来!”,而像朱迪·丹奇和迈克尔·甘本这样的人会对头麦的拐杖不屑一顾。但是年轻人对表演艺术越来越懒惰,就像戏剧学校对表演艺术的教学越来越漫不经心一样。
奥利维尔奖现在承认声音设计师的巨大成就是对的,但戏剧体验核心的一些发自内心的直接交流正在被他们的独创性所牺牲。我们的耳朵正在失去与真实事物的联系。
订阅3个月
NTHS 3英镑
每周注册两篇文章
已经是订阅者了?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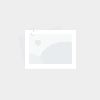







有话要说...